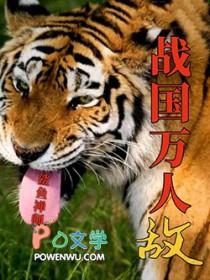天翼中文>风华辩 > 第114章 决裂(第1页)
第114章 决裂(第1页)
少年这边也好不到哪去,他本是要离开的,谁知刚准备下楼,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惨叫。
他疑惑地转过身,却见双目猩红的李子由突然朝他扑了过来,而他的双手上沾满了黑的血。
他分明没有下狠手,李子由手上为何会有血?
他及时躲闪到一旁,李子由扑了空后,又猛然间转过身,正巧与他的手擦了个边。
手背上沾到了一点血,他立马感到一阵灼痛感,他低下头,便见那点血正逐渐褪为无色。
李子由再次扑了过来,按理说他是能轻易躲开的,谁料整个身躯竟僵硬得不能动弹了。
李子由那么一扑,他便没稳住重心,几乎朝楼梯口栽去,而下一刻,又及时被人拉住了。
少年脱力似的软了身子,陆致宇顺势蹲下身查看他的状况。
谢子婴无力地单膝跪地,再抬眼时,眼瞳已经恢复如常,还清明了不少,他有气无力地唤了一声,“陆大哥?”
谢子婴意识很清醒,还拥有那家伙的记忆,他做了什么自己看得一清二楚。
一时间,面对这些或朋友或不待见他的孔铭弟子,他忽然觉得没什么可说的了,便扒拉开陆致宇,自行站起身离开了。
谢子婴一边沉思方才的一幕幕,一边往楼下走,没注意有人迎面上了楼,还拉了他一把,“子婴?”
谢子婴下意识地唤道:“夏轻。”
为什么夏轻也在?
陆致宇并未跟所有弟子讲重聚一事,而其他人就不一定了。
还有洛子规答应过要来,却为何迟迟没有出现?
两人又自然而然地相对上下楼,夏轻却往他手里塞了张纸条。
谢子婴没忍住叫了他一声,道:“你来这里……”
夏轻稍微一皱眉,道:“我来结束三年前的恩怨。”
这话什么意思?
谢子婴正想问出口,被夏轻打断道:“我先走了。”
又像是不欢而散。
谢子婴心一沉,麻木地走出客栈,却现外面下起了雨,只好转身找店主借伞。
趁店主找伞的功夫,谢子婴心事重重地打开了那张纸条,却看到上面写着一句话:酒肆外有人接应,离开!
谢子婴一脸懵,店主地见他呆,将伞递过来提醒道:“公子,伞!”
谢子婴将纸条收好,随口道了谢,没接,又改道上楼了。
谢子婴有点急不可耐,也难免加快了步伐,显得很匆忙。
若三年前他选择夏轻的人品,夏轻怎会被打成那样,而他与夏轻之间又何至于落到这个地步?
然而当他靠近了,却听见隔间里传来激烈的争吵声,仿佛是在比较谁声音更大、谁更凶一样,所有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不休。
谢子婴在门口正好听到一句话。
“这么闹有什么意思?要打就打吧!”
“子婴他爹是丞相,陶晋定不敢拿他怎么办,而若你们中谁得罪了陶晋,便相当于得罪了陶政。不就是怕得罪陶政,殃及你们的爹么?说啊!你们有几个不是这样想的?既然利用了人,怎么还好意思说子婴未满十六岁来替我们这些十八、九岁的背锅,不嫌丢人么?!”
青年冷笑了一声,“是啊,敢做不敢认是人的天性,一开始任谁都天不怕地不怕,一旦要承担责任了,就知道推给别人了!”
有人气不过,也站出来道:“对,你拿子婴当朋友了,不也扔下他了?事情已经生了,如今在这里马后炮又有什么意思?”
“就是啊,再说也不完全是我们的错,那还不是怪子婴,他当年若是肯忍一忍陶晋那疯子,哪还会有今天?如今你们生气又是给谁看的?”
“还有方才你们看到没有,谢禅把李子由打成那样,他走了倒是轻松,若是李子由告状,我们又得替他背锅!”
“说起来他这么厉害了,竟随手一掐就把人弄哑了,三年不见,他倒是能耐了。”
“可不是,若是一早我们就与他不对付,没准变成哑巴的人就是我们了!他跟李子由多大的仇恨要把他弄成那样,不就说了是他一两句,至于吗!?”
“至于!”有人忽然提高音量,还有些不容置疑,“我不知道子婴说了什么,但我知道每个人底线不一样……”
“你也有脸说这话!?”他还没说完,有人便气急败坏地打断了。
“当年也不知道是谁,骂谢禅骂得那么凶,还说什么‘我嫉妒你,我恨你,你光芒万丈,可曾记得我哥’,天哪恶心死了,我都没这么矫情!”
“就是,这里有你什么话?今日这是怎么了,陆大哥也不小心些,妖风太大,竟把你们几个吹来了。听说谢伯……谢文诚手里有阴符令,阴符令又给了谢禅,你们别都是为了阴符令来的吧!?”
盛垣嗤笑了一声,道:“都说墙倒众人推,从前一口一个子婴、谢伯父的叫,而今就变成了谢禅、谢文诚了?也是,人与人之间除了逢场作戏,毕竟还有相互作践!!”
有人没好气地怼了回去,道:“你说得都对,都是我们的错行了吧!就你最干净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