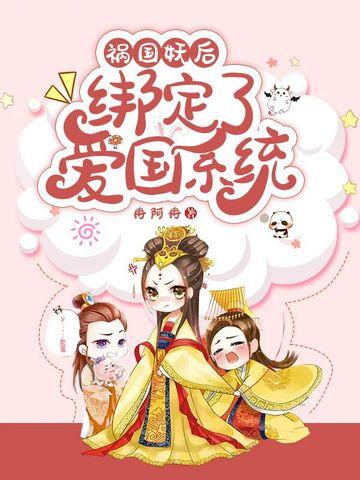天翼中文>重生觅良婿,偏执权臣他总想抢亲 > 第37章 好姐姐(第1页)
第37章 好姐姐(第1页)
白怀瑾踏进家门时,整张脸阴沉得可怕,可怖的是他颧骨处那道渗血的淤痕。
管家捧着药膏匣子碎步上前,白怀瑾一把抓过青瓷药瓶。
老仆望着他青紫的颧骨欲言又止:“公子这伤。。。可要唤个丫头来伺候上药?”
“用不着。”青年甩下三个字径自往内室走,衣袖带起一阵冷风。
十年前红绡帐里的温言犹在耳畔。
桑知漪总爱伏在他汗湿的胸膛上,指尖勾画着肌理纹路,发间茉莉香混着情事后的旖旎气息。”你这副身子是我的。”
她忽地撑起身子,杏眼映着烛火潋滟生光,“不许让旁人碰。”
他当时故意逗她:“连伺候梳洗的丫鬟都不行?”
“自然不行!”她急得衣襟滑落半边,露出雪脯上点点红痕,“既结发为夫妻,就该是彼此唯一的!”这话里分明藏着对纳妾的忌惮。
那时他当是闺中情趣。世间男子哪个不是三妻四妾?待年岁渐长情爱转淡,她或许还会主动替他物色几房知冷热的妾室。
他将这念头说与她听,气得她杏眼圆睁:“我永不会这般!此生只你一人!”
后来他官至宰辅,多少美人自荐枕席。可每每对上她们含情眉眼,总会想起红烛下那双倔强的杏核眼。即便后来夫妻离心,他仍守着这句玩笑般的诺言。
药油刺痛伤处,铜镜里映出他讥诮的唇角。
这世上哪有什么感同身受?除非你也尝过剜心之痛。他守着承诺,可许誓的人早将誓言碾作尘土。
夜半惊梦,他又见前世那间昏暗厢房。
素衣女子蜷在榻上发抖,突然呕出大口黑血。他惊坐而起,冷汗浸透中衣,耳畔还回响着那日戏楼上的话——
“我们和离罢。”
那日细雨绵绵,她眼底的绝望像淬了毒的银针。他竟就那样转身离去,任她独自枯坐半日。
如今想来,她临去时该有多恨?
白怀瑾猛地掀开锦被。
漆黑夜色里传来窸窣响动,守夜小厮揉着眼看见主子胡乱系着外袍冲出门去,衣带在风中翻飞如断翅的蝶。
……
桑知漪第二日没能见到谢钧钰来接她。
天刚亮透,谢府的侍卫裘熙便来桑府传话:“大人这两日在兵马司忙得脱不开身,铺子的事若小姐不放心,属下送您过去。”
谢钧钰往日从未失约过,桑知漪捏着茶盏的手指紧了紧:“怎么突然这般忙碌?昨日分明没听他提起。”
裘熙垂首盯着青砖地面,掩盖眸中的心虚:“今早临时出的急差。”
桑知漪心里已猜着七八分,待裘熙退下后便往兄长院里寻去。
谁料桑知胤竟彻夜未归,只留个小厮回禀说宿在友人府上。这下她愈发笃定昨夜定是出了变故——谢钧钰躲着她,十有八九与白怀瑾脱不了干系。
想起昨夜被那人堵在暗巷的情形,桑知漪扯着帕子狠狠擦拭脖颈。
从前爱慕他时,只当那些偏执行径是情深难抑;如今情意散了,倒显出几分可憎的占有欲来。她尚不知晓白怀瑾今晨又来寻过她,更不晓得对方被魏婆子拦在门外时,生生将新漆的门框抠出五个指印。
直到第三日晌午,谢钧钰顶着左颧骨青紫的瘀痕登门。
桑知漪凑近了细瞧,才发觉他嘴角还藏着道结痂的裂口。